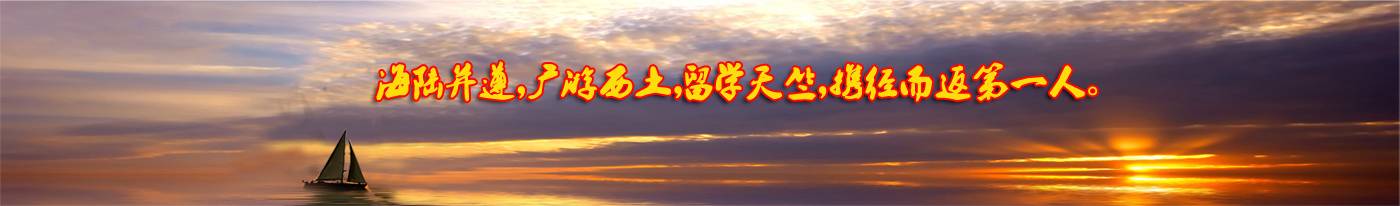
侯慧明:法显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影响
来源:
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
日期:2018-10-19
点击: 属于:学术论坛
作者:
摘要:法显西行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尤其是《佛国记》的广泛流传,其中记述之印度佛法盛况对中国佛教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其翻译之《大般泥洹经》为般若学与涅槃学的融通开启机缘,其翻译的律藏经典促进了中国佛教僧团建设,也促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和民间化。
关键词:法显 佛教 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断进行改造,使其在义理思想、仪范轨制等诸多方面都发生变化,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民族性和文化品格而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风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僧人为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显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武阳人。3岁被送至江陵辛寺为沙弥,其后正式出家。法显为人志行明敏,行谊整肃。由于有感于当时佛经不甚完备,戒律多谬误及残缺,故矢志往天竺求经。东晋隆安五年 (399),与同学慧景、道整等由长安出发,经陕西陇县“夏坐”,至张掖,与智严等僧人相遇,相约同行。至敦煌后,停留月余,然后进入一千五百里的流沙路。 后到达鄯善,西北行至乌夷国,法显在此稽留三个月,再至于阗,在此复停留达三个月,参观当地庄严殊胜之行像仪式,其后继续西行,入葱岭,过印度河,到达北印度乌苌国,开始他为时六年多的周游印度,循礼佛迹的旅程。403年,法显到达中印度摩竭陀国,在此参观佛迹、学梵语、写律经,得《摩诃僧祇律》一部。法显再沿恒河南下,到达多摩梨帝国,在此写经画像。 两年后,到达狮子国,在此逗留两年,求得律部《弥沙塞律》藏本及其它经本。义熙七年 (411),法显坐商船东归,途遇大风,大船损毁,只得把随身行李抛弃,仅保存所得经像,飘流海上,几经艰辛,共历八十余日,才到达山东青州,义熙十年 (414年)七月至建康,在中国翻译佛经,并完成纪行稿,423年,卒于荆州。
一、《佛国记》中对释迦牟尼佛及舍利的崇拜,促发了中国佛教日益向民间化方向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造像与舍利崇拜也渐次兴起,至少在三国时期,舍利实物以及舍利崇拜思想已经传入中国,《高僧传》中讲到江南最早的建初寺建立时提到康僧会以“神通”感得舍利赢得了孙权的崇奉,而这里的“神通”主要是舍利的“神异”。这则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察,但其逻辑理路基本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法显归国后,根据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佛国记》,其中记载了西域诸国及印度建立佛塔寺庙、释迦造像、供养佛顶骨、佛牙,膜拜佛钵、佛杖等活动情形。此类活动都是佛教民间化的表现形式。种种佛教崇礼膜拜形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效仿之楷模,影响中国佛教向民间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包含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对佛陀的遗骨、遗物、遗迹的崇拜
有关佛钵、法杖等遗物的记载不少,这些遗物被赋予了神秘的功德。如《佛国记》中载:“揵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佛钵即在此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挍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1]可见,佛钵在弗楼沙国的传奇故事以及所包含的所谓神异功德威力已为人们所认可,并成为北印度一种佛教信仰的民间化形态。供养的佛锡杖也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那竭国(今阿富汗)城东北一由延,到一
[1]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3页。
谷口有佛锡杖,亦起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旃檀作,长丈六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养。彼国土俗亢旱,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即大雨。”[1]《佛国记》中这些描述佛锡杖、衣服所具有神奇力量的内容,很容易使一般民众为获得庇护而产生浓厚的兴趣,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佛舍利的供养在印度也比较兴盛,如在那竭国醯罗城供养佛顶骨,《佛国记》载:“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国界醯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校饰。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椹,碪下,琉璃钟覆上,皆珠玑校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螺,敲铜钹。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 [2]另外,《佛国记》中还记载,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也有阿育王建造的舍利塔和石柱,竭叉国(今喀什)有对石制佛唾和佛牙的供养塔,僧伽施国(今印度北方邦法鲁巴克德),有收藏佛发、佛爪的大塔等。从《佛国记》中的这些记载可见,释迦灭度之后的印度以及西域一带,供养礼敬释迦的遗骨、遗物、遗迹,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第二种是对佛、菩萨造像的崇拜
有关佛像的供养,《佛国记》中有不少记载。如在西北天竺的陀历国有木制的佛像,曰:“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3]又如在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翟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腕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与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焚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摇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其,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曰行像。四月一曰为始,至十四曰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4]再如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无畏山僧伽蓝中也供有青玉塑像。可见,这些佛像的形体、容貌和姿仪皆祥和、宁静、端祥、庄严,起到了所谓“人神沟通”的桥梁作用,并已被大众所接受。
第三种是对石柱、石窟的礼敬
有关石窟的礼敬,在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有石窟的记载。《佛国记》中曰:“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释将天乐般遮弹琴乐佛处。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蓝。¼¼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未至头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郮鹫,住窟前恐阿难。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存,故曰‘郮鹫窟山’。窟前有四佛坐处。又诸罗汉各各有石窟坐禅处,动有数百。佛在石室前,东西经行。调达于山北崄巇间,横掷其石伤佛足指处,石犹在。” 可见,在当时的印度石窟中,内容多是对佛陀生前说法的回忆和信仰。
《佛国记》中介绍这些具有“神奇功能”的供养物,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佛教向民间化的发展,有些至今仍深有影响。如佛足印的崇拜,法显度过印度河,到了乌苌国。“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已。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拜对象,直到玄奘时代依然十分流行。
[1]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9页。
[2]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8页。
[3]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2页。
[4]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书中还记载了北印度的佛本生遗迹,例如在宿呵多国,法显就考察了一种本生信仰:“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即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此处起塔,金银挍饰。”[1]此外,法显在北印度还看到与此相同的另外几处本生信仰遗迹。在犍陀卫国,“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金银挍饰”[2]。在竺剎尸罗,“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复东行二日,至投身餧饿虎处” [3]。佛本生故事中的割肉喂鸽、舍身施虎、以眼施人、以头施人等内容,不但在佛教界成为激励僧人行善布施的榜样,而且成为中国佛教壁画和塑像重要素材,对佛教走向民间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法显乘坐商船,在狮子国遇到困难时,却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4]法显在危难之际祈求观音,是印度佛教信仰之风的播散,之后观音信仰在中国也迅速传播,成为佛教中影响最大的神灵之一。
舍利崇拜在东晋以后逐渐盛行,极有可能是受到法显东归后撰写之《佛国记》的影响。《佛国记》中,大量记载了印度各地造塔供养佛顶骨、佛齿等佛舍利的膜拜形式,如在那竭国酰罗城供养佛顶骨,《佛国记》载:“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国界酰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校饰,国王敬重顶骨。”[5]在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有阿育王建的佛舍利塔及建立的石柱,葱岭以东的竭叉国(今喀什)见到有对石制的佛唾及佛齿的供养塔,在中天竺的僧伽施国(今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巴克德),见到收藏佛发、佛爪的塔等。从《佛国记》的载述可见,5世纪左右的印度,供养礼敬佛的遗骨、遗物、遗迹,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佛教发源地的这种崇拜形式在佛教 信仰日益发展的中国势必成为佛教徒争相师法之典范,深刻影响中国佛教向民间化方向的发展。
从较早出现在中国的这些“舍利故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舍利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所谓的“感得”,颇富传奇色彩,增加了舍利信仰的神秘性,另外的途径或从西域或者从印度传来,增加了舍利信仰的正统性;其二,舍利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僧人身上,少数发生在外国僧人身上,说明源之于印度的这种佛教信仰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国僧人的认可,而且已经被作为扩大佛教信仰、争取信众的一种重要宣传手段;其三,舍利信仰均伴随有不可思议的所谓“神异”现象出现,助推了舍利信仰的扩散;其四,百姓信仰倍增,由下而上、由僧而俗直至倾服帝王,帝王崇信又使舍利信仰影响世风。
《高僧传》所载孙权向康僧会索取舍利之事,神异成分浓厚,值得怀疑。中国历史上崇信舍利的皇帝较为可信者当首推梁武帝。梁武帝也揭开了中国帝王崇奉舍利的先河。梁武帝崇佛,对舍利尤为崇信,大同四年(538)秋七月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如来真形舍利,大赦天下”[6]“大同五年(539),(扶南)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7]又“高祖曰: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设无碍大会,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眀和,京师倾属,观者百数十万人,所设金银供具等物竝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8]梁武帝是迎奉供养舍利最早的皇帝,直接成为隋唐时期帝王供养舍利的效仿对象。
[1]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9页。
[2]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0页。
[3]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2页。
[4]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42页。
[5]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8页。
[6](唐)姚思廉撰《梁书》卷3,中华书局,1974年,第82页。
[7](唐)姚思廉撰《梁书》卷54,中华书局,1974年,第790页。
[8](唐)姚思廉撰《梁书》卷54,中华书局,1974年,第792页。
二、法显回国后译经以及撰写的经论,推动着佛教义理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佛教自汉代开始,诸多义理在传到中国后,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
魏晋时代,佛教的般若学传到中国。般若学讲缘起性空,认为宇宙一切事物都是原因条件结合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正因为万事万物之缘起,因此也是性空的。佛教认为现象是有,本质是空,但性空离不开有,故缘起性空。这套理论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却很难理解它,在当时一些中土佛教学者中产生了疑惑,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例如,与僧肇、道生、道融并称为“关中四圣”的僧叡,在协助鸠摩罗什译完《妙法莲华经》之后,见经中说实归本,云佛寿无量,即便叹曰:“《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1]他还把《般若》与《法华》作了一番比较,认为:“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於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2]僧叡朦胧地意识到,似乎应该确立一个“实体”,而不能只在“空”中打转。般若不但是“破”(破除世惑),而且还应有所“立”(建立实体)。但是,这个应立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呢? 《法华》虽然讲到如来寿量长远,不过却并未论及佛身是常。因此,僧叡在《法华》中找不到完满的答案。
随着法显的西行,带回了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并被翻译出来,这个问题也逐渐有了答案。如慧叡在《喻疑论》中所言:“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金以莹明,显发可知。”[3]可见,大乘《大般涅槃经》涅槃佛性之明文,为当时的佛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但与此同时,《大般涅槃经》的译出也给当时的中土佛学界带来一些疑惑,并由此引发了晋宋之际中土佛教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其中“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的论争,成为当时乃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佛学界所面临的最核心的焦点问题。有的佛教学者,往往把般若学与涅槃学对立起来,以般若学的“空”否定涅槃学的“有”,以“人无我”否定“佛性我”,甚至把“佛性常住说”视为“神明不灭论”而加以指责。有的佛教学者则致力于般若学与涅槃学的会通工作。如道生,在注释《维摩诘经》的时候,即把“般若性空”所讲的“无我”与“涅槃妙有”所讲的“佛性我”会通起来,指出:“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4]在此,道生认为,虽然般若表面上说“无我”,但究其实质,说“无我”恰是为了表有“真我”。般若是通过扫一切相来显示实相,涅槃则直接以佛性来体明真际。因此,般若性空学说与涅槃佛性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一致的。这样,道生等人就把般若学与涅槃学在理论上相互结合,在般若学实相论基础之上来构建涅槃佛性论学说,为后来佛性论思想的发展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架构。
然而,追本溯源,促使中土佛教学者把“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的关系视作佛教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把实相与佛性联结起来的最初机缘,即在于法显所携归的《大般泥洹经》的译出。这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法显西行带回及翻译的律藏经典,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制度化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的传译,却独缺律典的传来。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249—253年),戒律始传中国。《高僧传》载:“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
[1]僧叡:《法华经后序》,《出三藏记集》卷八,中华书局,1995年,第306页。
[2]僧叡:《法华经后序》,《出三藏记集》卷八,中华书局,1995年,第307页。
[3]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中华书局,1995年,第235页。
[4]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三,《大正藏》第3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第354页。
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1]这表明当时中国的僧人缺乏戒律的约束,于是译出《僧祗戒心》戒本一卷,这是中国戒律之始。此后,在中国出现了依戒法而出家之制。《佛祖统纪》卷35载“汉魏以来,二众唯受三归,大僧沙弥曾无区别。昙摩迦罗乃上书乞行受戒法,与安息国沙门昙谛同在洛,出昙无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门朱士行为受戒之始。”[2]从此,中土僧团开始建立了传戒制度。
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团规模不断壮大,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尤其佛教戒律较为缺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道安认为,尽管大法东流,而佛教戒律却至为不全,“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3]所以,法显的西行求法,正是为了求取律典。《佛国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4]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的是戒律的完善,足以说明当时僧团中具备戒律规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没有戒律之约束,僧团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的局面,甚至会引起统治层的关注和不安。如《高僧传》卷六载:“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顺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5]只有僧团制定了规约,僧人的日常修持才能有约束,才会区别于世俗之人,也才能为统治者所接纳和认可。由此可见,法显西行求法对于中国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据《佛国记》的记载,他在天竺游历十余年间,在巴连弗邑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各一部,又在师子国得《弥沙塞律》一部。其中《摩诃僧祇众律》,在他回国后即与佛陀跋陀罗一起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弥沙塞律》则由稍后刘宋时的佛陀什和竺道生等译出;《萨婆多众律》则因在法显回国时已由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译出了《十诵律》,所以未再有传译。即此可见,法显为中国汉地僧团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主要依据,充实僧团制度的建设。纵然,唐代以降,中国律宗是以《四分律》为根本,但法显对中国佛教戒律的发展完善仍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佛国记》中对印度佛教供养制度的记载,也影响着中国佛教供养制度和寺院经济的发展
佛教创始之初,僧侣就以乞食为生,需要信众供养,《佛国记》也有记载。如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百余僧,日将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6]又如在那竭国界醯罗城,“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椹椹下,琉璃钟覆上,皆珠玑校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螺,敲铜钹。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惓。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精舍门前,朝朝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
[1]慧皎:《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第13页。
[2]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五,《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第332页。
[3]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中华书局,1995年,第333页。
[4]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5]慧皎:《高僧传》卷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240页。
[6]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3页。
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精舍处方四十步,虽复天震地裂,此处不动。”[1]又如到达竭叉国,“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华,著缯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诸群臣,设供供养。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毡、种种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赎。”[2]
除国王对佛教的信仰外,还有居士、商人及普通民众等。如师子国“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本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3]又如在摩头罗国,“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阙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作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客僧往到,旧僧迎逆。代檐衣钵,给洗足水,涂足油,与非时浆。须臾,息已,复问其腊数。次第得房舍、卧具,种种如法。”[4]可见,当时印度僧团受王室及贵族之供奉,财富积聚,已非昔日可比,因而寺院经济较为发达。
《佛国记》中对印度佛教的供养制度的记载,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在早期,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经济,主要靠朝廷和民间的资助或供养。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上层统治者大多笃信佛教,给予其巨额的经济支持。《佛祖统纪》卷六载,陈宣帝太建九年(577),令“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5]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立大规模斋会,供养寺院金银供具,并施钱一千万作为寺院基业。[6]除此而外,一些信佛的王公贵族也对寺院、僧人进行供养,甚至民间的信众“糜费巨亿而不吝”[7]。这些说明此时佛教已经不断地深入民间,商贾、平民、贫民、流民等阶层便成为信仰的主体。他们之所以愿意花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来宣扬佛教,主要目的仍是为祈求“功德”与“福田”,能使其家族继续保持(或改善)此世的命运、以及死后上生于兜率天或西方净土。从当时之造像铭、供养画像的题记中可看到这样的祈求,如《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曰:“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饰仪丽晖,以□(释)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德隆)运表。皇太后、皇太子□□(延祚)无穷。群辽百辟,存亡宗□(亲),延沈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8]又如《刘洛真造像记》曰:“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二区,使亡父母托生紫微安乐之处。还愿七世父母,师僧眷属,见在居门,老者延年,少者益寿,使法□□生,一时成佛,咸愿如是。”[9]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都说明中国佛教在日益走向大众化,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五、法显西行中体现出的爱国护教之情感,感染了此后无数的僧人,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与发展
法显并非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但其不畏艰难险阻,不惧生死危难的行迹,都被详细记录于《佛国记》之中,“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10]其勇猛精进,为法忘躯的精神,对后世佛教信徒产生巨大的榜样作用。法显归国后不久,昙无竭与僧猛、昙朗等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
[1]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38页。
[2]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7页。
[3]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4页。
[4]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47页。
[5]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第182页。
[6]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546页。
[7]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2028页。
[8]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1980年第1期。
[9]王昶:《金石萃编》(第一册)卷二十七,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5年,第527页。
[10]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53页。
有忘身之誓,……发迹北土远适西方。”[①]宋云、惠生等人也紧随其后,并著有行记。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亦受到法显精神的感染,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法师讲述曰:“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曌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②]由此可见,法显西行对后代僧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像法显、玄奘这样的僧人努力下,佛教才在中国得以推陈出新,发展壮大。
《佛国记》中我们多次看到法显触景生情、思念故乡的描述,体现出法显爱国与爱教的精神。如“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③]在航行多次遇到危险时,“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④]法显睹物思乡的真挚情感,以汉地众僧为念的涓涓心思,无不流露出他对祖国的思念与眷恋,对中国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这是一中爱国爱教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代树立了榜样,影响深远。
法显西行求法,将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记录于《佛国记》之中,印度佛教的崇拜形式、供养制度,特别是戒律经典对中国佛教的制度化以及向民间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法显的舍身求法,不怯不疑、为法忘己,不怖不畏的精神和功业,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丰碑。
[①]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95年,第581页。
[②]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第222页。
[③]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8页。
[④]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42页。
作者简介:侯慧明,男,1977年生,山西寿阳人。宗教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山西佛教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佛教研究。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山西佛教壁画调查与研究”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唐密曼荼罗法研究”1项,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五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1项,山西省创新人才项目“山西道教壁画调查与研究”1项,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五台山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专著《胎藏曼荼罗研究》1部,参编著作三部,获山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百部篇一等奖一项。
